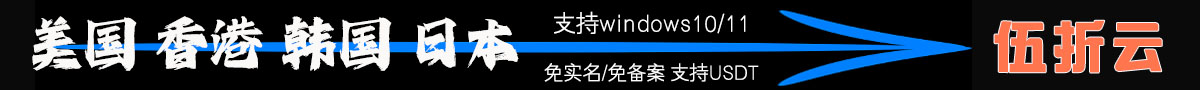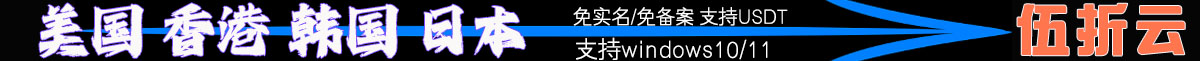曾经的“芯片之王”如今在哪里?
本文访谈对象是Dan Kim,现任TechInsights首席战略官,曾担任美国商务部CHIPS for America项目首席经济学家与战略规划主任。
在加入政府部门前,Kim曾任SK海力士首席经济学家、高通经济战略总监,以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高级国际经济学家。他在CHIPS法案执行期间,直接参与了对TSMC、Intel、三星等主要芯片制造商的尽职调查与资金分配决策,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技术路线图、客户关系与地缘政治风险有第一手观察。
苹果、英伟达或高通决定与某家代工厂合作时,它们实际上是在承诺:未来两到三代产品都将基于该厂商的工艺节点开发。
这种承诺一旦做出,至少需要两年才能完成设计迁出,但在快速迭代的消费电子与AI芯片市场,两年足以错失一个产品周期。
客户告诉我们,他们非常享受与TSMC的合作,因为TSMC既协作又可靠。——这是Kim在执行CHIPS法案尽职调查时,从几乎所有无晶圆厂芯片公司那里听到的一致反馈。
正如Facebook通过广告平台催生了依赖其存在的电商企业,TSMC通过可靠的代工服务,让苹果、英伟达、AMD等公司得以专注于芯片设计而非制造。
苹果、英伟达、AMD等科技公司的产品开发周期、技术路线图、甚至公司的组织架构,都是围绕TSMC会按时交付先进制程芯片这个假设来构建的。
FinFET(Fin Field-Effect Transistor,鳍式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3D晶体管架构,是芯片制造工艺从平面晶体管向立体结构演进的关键技术。
传统晶体管是平面的,电流在硅片表面流动;FinFET则将晶体管的导电沟道做成垂直的鳍状结构(像鱼鳍一样突起),栅极从三面包围这个鳍,形成更好的电流控制,可以在更小的尺寸下保持性能。
在先进制程领域,竞争被称为流血的前沿(bleeding edge),需要持续烧钱才能维持。
当客户评估是否将订单转移到Intel时,他们会问:Intel有足够的资金在未来五年持续投入吗?
这个问题在Pat Gelsinger时代尤为突出——他承诺四年五个节点,试图通过激进扩张重建信任,但这种策略反而加剧了财务压力。
Pat Gelsinger(帕特·基辛格)是Intel前CEO(2021-2024年),Intel传奇工程师出身,曾主导80486处理器开发。他在2021年回归Intel,试图通过四年五个节点的激进战略重振Intel代工业务,但因财务压力和战略分歧于2024年底离任
Pat Gelsinger的先建产能再吸引客户策略,本质上是一场豪赌。
他的逻辑是:如果18A节点(1.8纳米制程技术,用于对标TSMC)技术成功,但没有足够产能,客户依然不会来;因此必须同时押注技术与产能。
新任CEO Lip-Bu Tan的策略转向先有客户再建产能,但这又陷入了经典的鸡生蛋问题:
Lip-Bu Tan(陈立武)是Intel现任CEO(2024年底接任),马来西亚华裔企业家,EDA软件巨头Cadence前CEO,以务实著称
2013年前后,Intel面临关键抉择:是否进入移动芯片代工市场。当时苹果正在寻找A系列芯片的第二供应商,Intel有机会切入。但管理层认为代工业务利润率低、会分散资源,最终选择专注PC与服务器CPU。
AI基础设施的爆发性需求与晶体管架构的代际切换(从FinFET到全栅极、背面供电)几乎在同一时间窗口内发生。
先通过AI芯片订单建立客户信任,再利用架构切换实现技术反超。但当两者重叠时,客户面临的是在新架构上选择未经验证的Intel,还是选择已验证但需要等待的TSMC——答案显而易见。
时间窗口的压缩,使得Intel必须在18到24个月内同时解决上文提到的文化转型、财务可持续性与技术交付三个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迟,都会错过整个生态位的形成期。
技术窗口的存在不等于商业机会的兑现。——Kim的这句话揭示了Intel困境的本质: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少把握机会的时间与资源。
当台积电在2010年代通过28纳米、16纳米节点逐步巩固代工霸主地位时,Intel选择了坚守IDM(垂直整合)模式。这一选择在PC与服务器CPU市场尚能自洽。
但当移动与AI成为芯片需求的主导力量时,缺乏代工生态的Intel发现自己既无客户基础,也无文化准备,更无财务余地来快速转身。
Kim回忆,在执行CHIPS法案期间,一位资深参议员明确表示:如果需要救Intel,国会会另行立法,但CHIPS的任务是把制造能力带回美国。
这一定位在2022到2023年是清晰的:支持多家厂商在美建厂,分散风险,而非押注单一企业。
与此同时,TSMC在3纳米节点的量产进度超出预期,客户对其新架构路线图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原本存在的技术竞争窗口正在快速关闭。
此时,问题不再是是否应该支持Intel,而是如果不立即行动,Intel是否会彻底失去继续竞争的能力。
政府持股相当于提供了一个隐性担保——即使商业上遇到困难,国家战略需求会确保Intel的存续。
我们需要给Intel足够的财务跑道来执行战略,这改变了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只是资助哪些工厂,而是如何确保竞争者能活到终点。
但支持者会反驳:在半导体这样的战略产业,市场失灵已经发生——TSMC的自然垄断地位使得任何新进入者都面临无法获得初始客户的死锁,而纯市场机制无法打破这一僵局。
政府介入的目标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创造一个客户愿意尝试Intel的最小可信环境。
Kim在访谈中提出:现代社会建立在陌生人之间的信任之上——你使用陌生人制造的电梯、驾驶陌生人组装的汽车、服用陌生人研发的药物。
与此同时,过度的管制可能促使中国构建完全独立的技术栈。Kim在访谈中提到,稀土供应链就是一个教训:当中国垄断稀土加工能力后,美国试图重建供应链的成本远高于当初维持多元化供应的成本。
这一困境没有简单答案。它要求决策者在短期商业利益与长期战略风险技术开放与安全管控单边行动与多边协调之间反复权衡。
Pat Gelsinger是一位技术天才与鼓舞人心的领导者,但他的乐观在Intel的特定情境下成为负担。
当你需要吸引客户时,必须展现愿景与信心;但当你的公司正处于需要重建信任的阶段时,过度承诺会适得其反。
Gelsinger试图用激进的路线图证明Intel的决心,但客户需要的不是宏大叙事,而是承诺一个路灯,结果打到街灯的稳健超预期。
对比之下,Elon Musk可以谈论机器人出租车与火星殖民,因为他已经用特斯拉与SpaceX证明了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能力。
Intel在2020年代初期不具备这种信用储备——它刚刚经历了10纳米节点的多年延迟、市场份额被AMD蚕食、代工业务从零起步。
新任CEO Lip-Bu Tan的务实主义更符合当前Intel的处境,但它也带来新的挑战。
先用现有产能服务小批量订单,用实际交付记录建立信任,再根据订单增长逐步扩产。这种路径更慢,但风险更可控。
但代工业务的本质是服务业,技术只是入场券,真正的护城河是客户关系、流程可靠性与生态系统效应。
TSMC的成功不仅因为技术,更因为它花了30年时间将客户成功嵌入组织DNA。Intel需要的是懂得如何在服务业中竞争的领导者。
它要求Intel从我们制造最好的芯片转向我们帮助客户制造最好的芯片。
前者是产品思维,后者是平台思维。前者的成功标准是自家产品的性能,后者的成功标准是客户产品的成功。